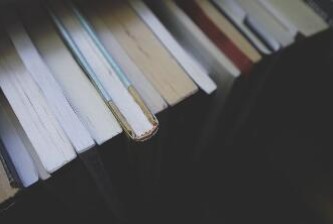三星堆遗址,会不会就是一直都未找到的夏朝都城
这是一个已经156个回答的问题。作为一个研究三星堆多年的人,我知道这个问题并不那么容易一下说清楚。这里,我就试着回答一下:
题主问题:三星堆遗址会不会就是一直都未找到的夏朝都城?
我的答案:三星堆文化分四期,其第三期的青铜文明确实属于夏朝都城。
具体分析过程:
第一,名不正则不顺。在正式进入分析前,我们必须要先处理相关的概念。
题主问题中的”夏朝“属于历史学概念,”三星堆遗址“属于考古学概念。相对来说,三星堆遗址的历史分期是比较清楚的。三星堆文化共分四期:第一期,大约在公元前2800年到前2000年;第二期,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到前1600年;第三期,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到前1200年;第四期为公元前1200年之后。其中,著名的三星堆青铜文明属于三星堆文化的第三期,大家说三星堆文明的时候,也往往指的是这个阶段。
按照三星堆的分期,显然我们不应该认为三星堆遗址与夏朝都城有关。然而,问题就出现在我们传统观念中的夏朝体系本身存有疑问。众所周知,当大家说到夏史体系时,首先想到的都是《史记》。《史记》视禹为夏的开端,但先秦文献《竹书纪年》却视黄帝为夏的开端。这说明《史记》理解的夏与《竹书纪年》理解的夏是不同的。
此外,《墨子》视虞、夏为一代,清华简《楚居》说楚人祖先季连以盘庚孙女为妇,《山海经》被称为禹益之书却记载了成汤事迹,这些记载都与《史记》的夏史体系存在冲突。同时,目前我们已知的一批重要考古文化,如三星堆、金沙、盘龙城、新干、齐家文化等也无法在《史记》的历史体系中得到合理解释。同时,用《史记》体系我们也无法解释中国大量西部民族的形成,无法解释中国文化形成的脉络,无法解释早期中国与周边文化的互动关系。基于这些问题,笔者在长期的研究中,提出了夏与商周并行、夏分三段的观点。
第二,夏与商周并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夏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包括齐家文化、石峁文化、二里头文化等,王都可能是石峁遗址;第二个阶段,为三星堆青铜文化,第三个阶段,是金沙文化。也就是说,按照这个体系,三星堆遗址确实属于夏朝都城。
第三,那么,笔者的观点可以被证实吗?这里我举几个例:
(1)按照笔者的观点,三星堆的毁灭就是《左传》中提到的后羿代夏。三星堆有青铜神树,出土时完全被砸碎,德裔美籍学者罗泰把这一事件与”后羿射日“神话联系了起来。事实上,从文献整理来看,确实可以看出“后羿代夏”事件逐渐演化为“后羿射日”的文献痕迹。
(2)根据《左传》记载,后羿代夏事件之后,又有少康中兴事件发生。少康曾担任有仍氏牧正,传世文献又有少康制酒的记载,这些记载正好可与三星堆毁灭事件发生后出现的竹瓦街窖藏青铜器铭文实现对读。具体论述可以参阅笔者发在头条的文章《从历史语言学破解夏代王族的自称之谜:太阳家族与开明传说(中)》。
(3)按照传世文献的记载,大禹治水事件因何发生,伊雒竭夏亡是怎么回事,《禹贡》的真伪如何,以及《蜀王本纪》为何与中原传说具有明显的对应性,都是过去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按照笔者建立的夏与商周并行体系,则可以知道大禹所治之水其实是由大地震引发的,所治水域为岷江流域,大禹即蜀地文献的杜宇。具体论述可以参阅笔者的文章:《夏代末年的岷山地震与大禹治水的传说》。
(4)《山海经》的形成,在隋唐以前一直认为与禹、益有关,而唐以后屡被质疑。而笔者运用“夏与商周并行体系”则肯定了《山海经》出自禹益是有历史根据的,并较好地解释了《山海经》的成书问题。具体可以参阅:《三星堆文明是被遗忘的异世界吗?论大禹治水和《山海经》的形成》。
围绕着”夏与商周并行“的观点,笔者已经在头条号发布大量文章。后续文章在笔者整理后,也将陆续发布出来。这里不再一一细举。
总之,当我们重建夏史体系之后,会发现先秦文献与《史记》体系原来存在冲突的地方现在可以更好解释,西部许多民族的形成也可以得到更好的认识,同时,早期中国与周边文化的互动关系也可以得到更好理解。因此,根据这些研究,笔者的结论是:三星堆遗址确实中国人一直在寻找的其中一处夏都。
以上观点,欢迎大家的讨论。如果朋友们对三星堆、先秦史以及《山海经》研究感兴趣的,也可以关注我。我的口号是:研究三星堆,关注古史微。最后,请大家记得点赞哦。
这个问题问得多少有些让人啼笑皆非,提问之人可能连中国历史的基本方位都没有搞清楚。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两个概念,一是什么是三星堆?二是夏朝的范围。先说三星堆遗址,它的发掘地在四川的广汉,它被誉为中国20世纪考古发现的惊天之作,其范围之大,时间之长,内容之丰富,都是极为罕见的。
▲:三星堆遗址发现与考古挖掘
三星堆遗址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而夏朝呢?它是中国历史上世袭制朝代的开始,也就是说,我们平时所说的家天下,就是从夏朝开始的。
夏朝的范围涵盖了今天的河南、山西、山东、湖北和河北部分地区,也就是我们一直以来所说的中原地区,这一点是史书认定了的。
夏朝都城十七次迁移,但都是在今天河南省境内转来转去,从来没有出过河南省。所以三星堆遗址跟夏朝可以说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三星堆遗址所展现的是古蜀国文化。
▲:考古学家对遗址进行清理
而在公元前2000多年的时候,古蜀国还被称为蛮荒之地,那里的人民被称为蛮人,为中原人所不齿,双方没有任何交集。在这种情况下,三星堆遗址怎么可能成为夏朝都城,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多年来史学界会有三星堆遗址可能是夏朝都城的议论呢?原因就在于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原本只能在中原才能出现的文物,这是无法解释的事情。
既然两者没有交集,那么只属于中原文明的陶器和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三星堆遗址中呢?据此有人推测,早在几千年前,夏朝也许有另外一个都城设在蜀地,夏朝皇帝偶而会去一去,有陪都的性质,但是不是夏朝的都城。
▲:三星堆出土的怪异文物
但是也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因为我们现在的历史大部分都是根据史书得来的。
而最早的史书主要的着眼点又都集中在中原文明,对于中原以外的文明,史学家们要么是确实不知道,要么是装聋作哑,不去理会。
如果三星堆遗址真的是夏朝都城的话,那真的不得了,中国古代的历史全部要重新改写,包括《史记》在内的一大批史书全部要被推翻。
▲:果真如此,《史记》会被大量推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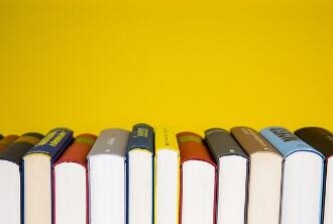
遗憾的是,关于三星堆,我们目前没有找到任何文字记载,只能根据所找到的文物来进行推敲,这需要时间。在没有定论之前,为了不出现史学界的混乱,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史书来确定一切。
因此,我认为,三星堆跟夏朝完全是两个概念,再做一个大胆的推测,那就是中国在夏朝之前,可能还存在一个文明时代,我们姑且称它为三星堆文明。
有一个史书依据,那就是《竹书纪年》这本书,书中提到大禹母亲是生于今天的四川北川,而大禹早年治水的地点也在四川,似乎可以印证中华最早的文明其实起自于四川的长江流域,而后才迁到中原,变成了夏朝。如果这个假设能够被史学家们印证的话,那么所有疑问都能够被解释得通了。
探讨三星堆与夏朝都城的关系,其实涉及到两个学科,历史学与考古学。夏朝都城属于历史学范畴,而三星堆遗址,则是考古学的内容,不同学科要对号入座,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首先,从历史学上来看
历史文献记载的夏朝核心区域在伊洛河流域,夏朝的先人,从鯀到禹,其活动中心一直在嵩山周围。夏朝立国之后,即便频繁迁都,从阳城(河南登封)、阳翟(河南禹州)、安邑(山西运城)、斟潯(河南洛阳)、老丘(河南开封),夏朝都城也一直未出中原的核心区域。也就是说,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历史学中记载的夏朝,就是以伊洛盆地为中心的中原王朝,这是探讨夏朝的前提,如果推翻历史文献的记载,那么这些探讨也就失去了意义。
所以,三星堆所在的巴蜀,无论发现遗存多么丰富的遗址,都不可能会是夏朝的都城。
其次,从考古学中来看
历史学记载了一种可能性,是一种前提,而考古学则是验证了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
三星堆文化是位于巴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存在时间大约是公元前2300年--前600年,按照其文化面貌,大致可以分为四期:
- 三星堆的前700年时间,三星堆人并没有创造出什么像样的文化;
- 一直到了距今3600年左右(相当于中原的夏、商之交),三星堆内部突然出现了具有中原文化特征的陶器等器物,自此,三星堆文化开始形成;
- 又过了500年,约公元前1100年左右,三星堆人学会了制造青铜器,此时已经来到了商末周初;
- 到了三星堆晚期,三星堆的宫殿、神庙被毁,大量居民迁往他处,三星堆遗址从都城跌落到普通聚落,三星堆文化至此消亡。
可见,三星堆开始形成自己的文化的时候,已经到了相当于夏朝要灭亡的时候了。而夏朝是青铜文化王朝,三星堆又是在夏朝灭亡之后,才掌握青铜文化的。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年表中来看(下图),三星堆文化(注意,是三星堆文化,不是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形成时间较晚)相当于中原的二里岗文化(早商文化),这就基本上表明,三星堆文化是晚于夏文化的。
那么三星堆文化与夏朝真没关系吗?答案是否定的,三星堆不可能是夏朝都城,但很可能是夏朝灭亡后夏文化的南迁,而且考古学中很支持这种观点:
三星堆的前世今生:两次“外族”迁入引巨变
三星堆的一生虽然大起大落,但脉络清晰。一般认为三星堆的前身是由成都平原的本土文化宝墩文化发展而来的,不过,近来的考古发掘却发现,三星堆文化并非简单的本土文化衍生而来,在大约3700年和3500年左右有两股外来文化迁入,严重影响了三星堆文化的发展。
考古显示:大约在3700年前,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因为某种原因走向衰落,而稍后四川本土的宝墩文化也在此时突然衰落,此时正值三星堆文化二、三期交替之时,考古观察到外来文化的入侵和本土文化的融合形成了三星堆文化,这些文化主要有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这种突变,很难用文化传播和影响来解释,伴随而来的可能是民族的迁徙和征服过程。
从出土的三星堆文物来看,三星堆文化面貌的表现主要是陶器、玉器和青铜器。简单来说:
陶器:盉、觚又都是二里头文化的重要礼器,二里头文化中期,三星堆突然出现极具二里头文化风貌的陶器,应是二里头文化南传的结果;
玉器:三星堆的玉器仅两个器物坑就出土了百余件,器类有璋、戈、琮、璧、瑗、环等,与二里头文化玉礼器种类基本相同,另外这些器物风格与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也极具渊源。
青铜器:三星堆铜器种类非常复杂,其中三星堆的铜牌饰、铜铃和铜尊等为典型的二里头文化,因为在三星堆以外地区,铜牌饰只在二里头文化的中心都邑二里头遗址的高等级墓葬中出土过,文化属性非常明确。此外三星堆大量人像、面具和神树等则是代表的地方因素青铜文化。
根据考古学揭示的内容,大致可以推知三星堆文化的前世今生:
- 在距今4300年左右,良渚文化灭亡,良渚人应该是顺着长江逆流而上,进入了石家河文化圈。
- 3700年前左右,东方的石家河文化衰落,而此后的三星堆文化,则明显观察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说明三星堆被石家河文化“侵入”,这也解释了三星堆文化中玉石文化中有明显良渚和石家河的痕迹。
- 而随后,二里头文化也进入成都平原共同形成了三星堆文化的面貌。
参考文献:
《再论川东长江沿岸的史前文化》,四川文物,2002年第5期;
《考古发现:三星堆文化的形成与夏人西迁》,《江汉考古》2005年第1期。